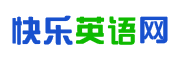我们再以性别为例。如西班牙语、法语、德语和俄语,这些语言不仅仅要求你考虑到朋友和邻居的性别,还要求你在一念之间决定众多没有生命的事物的阴阳性。比如说,一个法国男人的胡子(la barbe)有什么特别阴性的特质吗?为什么俄罗斯的水是“阴性的”,而你一旦把一个茶包浸入水里,“阴性”就变成了“阳性”?马克·吐温曾在有名的《可怕的德语》一文里就德语词汇中无规律可寻的词汇阴阳性而哀嚎咆哮,比如说,“萝卜”是阴性的,而“少女”是中性的。可是,尽管他声称德语词汇“阴阳性”系统中存在一些荒诞无稽,但真正异乎寻常的其实是英语,至少在欧洲一众语言中,只有英语是不去给萝卜或者茶杯分阴阳性的。那些给无生命事物阴阳定性的语言迫使说话者在提及这些事物时,就像谈论男女人一样。所有讲这种给事物定阴阳性的母语的人都会告诉你,一旦形成了习惯,你就不可能摆脱它的影响。我在用英语谈论一张床是软还是硬的时候,我会用“it”这代词,说“它”太软了,但因为我的母语是希伯来语,其实我脑子里会想到说“她”太软了。 那一声“她”,经由肺部行至喉门,一路都是阴性的,只是到了舌尖,真要说出口的时候才变成了中性的“它”。
The habits of mind that our culture has instilled in us from 24)infancy shape our25)orientation to the world and our emotional responses to the objects we encounter, and their consequences probably go far beyond what has been experimentally demonstrated so far; they may also have a marked impact on our beliefs, values and 26)ideologies. We may not know as yet how to measure these consequences directly or how to assess their contribution to cultural or political misunderstandings. But as a first step toward understanding one another, we can do better than pretending we all think the same.
我们所处的文化从幼年开始就向我们灌输的东西使我们的思维习惯得以形成,而这种习惯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对所遇的事物作出的情绪反应。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远远超出了已被科学实验证明的程度,它们还会深深影响我们的信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我们也许还不知道应如何直接衡量这些后果,也不知道如何评估有多少文化政治误解是由于这些思维习惯的影响而造成的。但要迈出人类间相互理解的第一步,我们起码不要再自欺欺人地认为人们的思维方式都是一致的了。